
2018-03-16 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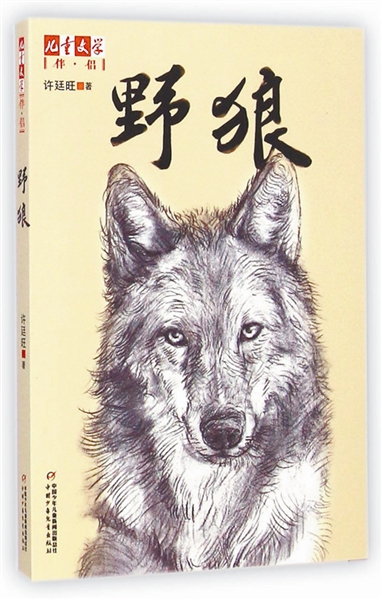
许廷旺作品《野狼》荣获科尔沁文化政府奖
许廷旺,第30届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儿童文学作家班)学员,1971年出生。于2003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创作题材广泛,曾创作幻想小说、校园幽默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和动物小说。在上百种刊物上发表500余篇儿童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近百部,500多万的文字。塑造的“林不几”“余晓鲁”“周大齐”等人物形象深受小读者的喜爱,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小说《五等小站》(原名《丑狗》)曾获第九届儿童文学擂台赛铜奖。小说《毛陶的暑斯生活》获《读友》征文优秀奖。侦探小说《雕塑上的魔咒》获《坊友》全国征文优秀奖。有科幻小说获《智慧少年》征文奖。有几十篇作品入选各种文集和年度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选。有作品入选《意林》《格言》等名刊。《大草甸》书稿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动物小说《山地羊军》《少年棋王》入选农村书屋工程。《鸽王红冠》入选江苏无锡新华书店推荐书目。动物小说《头羊》《火狐》《消逝的狼群》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幼崽制伏野猪崽后,杭盖再也想不出来既能培养幼崽格斗能力,又可以充当食物的猎物了。从这以后,幼崽就生活在饥饿与半饥饿中。饥饿能让幼崽保持强壮的体魄,又能保持旺盛的精力,格斗起来才会最勇敢,最凶悍,也最狠毒。果然,处在饥饿中的幼崽吼声如雷,弹跳功夫惊人。因一时疏忽,杭盖忘了用石头压住洞口,三头强壮的幼崽险些离开山洞。
幼崽出生一年后,离开了山洞。
杭盖移开一号洞口上的石头,“呼”,幼崽探出身子,整个身子塞满了洞口。杭盖抬腿就是一脚踹在幼崽身上。这一脚踹得结结实实,幼崽被踹痛了,一声怒吼。杭盖二话没说,抡起手臂粗的榆木棒子劈头盖脸砸了下去。幼崽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疼痛,也不知道躲避,任凭榆木棒子落在身上。它甩动大头,张开大嘴,扑向杭盖。杭盖不敢怠慢,再次挥棒砸去。幼崽眼疾口快,张嘴咬住棒子,杭盖往后一拉,“腾”,幼崽借机离开了山洞。
这头幼崽无论体型,还是被毛颜色,都像大犬旭日干的翻版。它的身材已接近成年大犬,被毛漆黑,纷长凌乱。目光中闪动着两团火焰,如两团复仇的火焰。杭盖给幼崽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乌西叶”
“乌西叶”在蒙古语里是“复仇”的意思。
幼崽乌西叶惊喜地打量着周围,渐渐地,一脸茫然。幼崽从小就生活在石洞里,几乎与世隔绝,每日见到的只有杭盖。当幼崽置身一个偌大的陌生环境中,对杭盖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尽管乌西叶刚刚经历了杭盖的毒打,可在第一时间里,它却摇头晃脑地向杭盖示好。
杭盖走向二号山洞时,幼崽乌西叶悄悄地跟在身后。
二号山洞的幼崽没等杭盖移走石头,就迫不及待地把头探了出来。杭盖飞起一脚,幼崽身子一趔趄,前肢和大头扒住洞口,幼崽发出一声不满的吼叫。杭盖恼羞成怒,挥起木棒砸在幼崽身上,幼崽一声惨叫,跌进山洞。
幼崽乌西叶不安地看着杭盖,二号山洞幼崽一探头时,幼崽乌西叶急匆匆地跑了过去,终于见到伙伴了!尽管此前,幼崽乌西叶已经熟悉了伙伴的吼声,但被困在山洞里,每个伙伴都显得那么神秘,相见那一刻,亲切与好感取代了神秘,想不到却被眼前这个高大男人破坏掉了。
幼崽乌西叶畏惧地看了杭盖一眼,凑到洞口,注视着洞里的伙伴。
杭盖走到三号洞口前,三号山洞的幼崽比前两个幼崽还要机敏,没等杭盖第二次举起榆木棒子,已置身地面上了。与前两个幼崽相比,三号山洞幼崽少挨了一棒,不过,前面的一脚一棒却是实实在在的。杭盖似乎知道这头幼崽机智灵敏,一脚一棒的惩罚格外用力。但三号幼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走到幼崽乌西叶身边,嘴巴与嘴巴凑到一起,嗅闻着,随后脖颈缠绕。
这仍是一头大型幼崽,只不过幼崽的被毛混合了大犬旭日干、狼的被毛颜色,是一种杂色。幼崽有高挑的四肢,紧凑的身子,修长的脖颈。从刚才的反应来看,幼崽机智灵敏,善于搏斗,不会有幼崽超过它。
杭盖喜不自禁,给幼崽起名“查黑干”。
“查黑干”在蒙古语里是“闪电”的意思。
来到地面上的幼崽乌西叶、查黑干发出欢快的吼叫,它们以地面主人的身份迎接来自山洞的伙伴。幼崽从山洞来到地面绝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要经过杭盖这一关,这一关也很简单,只要幼崽能禁得起一脚两棒,就可以离开山洞。一脚两棒是实实在在地毒打,如果它们在短短的这一刻能够抵抗住毒打,就说明有能力离开山洞。
毒打还有另一层含意:要绝对地服众杭盖。
幼崽离开山洞的刹那间,就像经历了一次九死一生。杭盖面露杀气和接踵而来的毒打,深深地印在幼崽的大脑里,直到多年以后,幼崽都无法忘记。
接下来幼崽的表现大不如人意,它们不是被杭盖一脚踢回山洞,就是架不住一记榆木棒子的毒打,狼狈地跌回到山洞里。
最后,杭盖来到九号山洞前。毒打引起的惨叫声大大影响了九号山洞幼崽的情绪,但恰恰相反,幼崽不仅没有害怕,而且连连吼叫,吼声一浪高过一浪。幼崽蹦跳着,兴奋极了,好像要冲出去,接受棍棒的洗理。
幼崽是从洞口里硬挤出来的。移走石头,挥棒击向幼崽消耗了杭盖太多的体力,在他勉强移开巨石时,幼崽强行挤了出来。即使这样,幼崽仍避免不了一脚猛踹。杭盖明显感觉到,这一脚就像踢在石头上,硬邦邦的。他怀疑忙中出错,踢在石头上了,低头一看,暗暗吃惊,幼崽安然无恙。因移开的巨石有限,空间也有限,幼崽正用力地向外移动着。
杭盖二话没说,抓住榆木棒子,劈头盖脸砸了下去。榆木棒子落在幼崽身上,幼崽哼叫一声,仿佛挠痒痒。毒打丝毫没有阻止幼崽的行动,昂着大头,挣扎着。杭盖眼前一亮,再次举起了榆木棒子,棒子落下去时,杭盖手轻轻一偏,榆木棒子紧擦着幼崽的头部飞了过去。
杭盖不忍心一记毒打给幼崽造成不必要的损伤,这可是他的复仇工具啊!
眼前的幼崽比所有的幼崽都魁梧,如果不是杭盖亲眼所见,误以为这是一头成年的大型猛犬。幼崽不仅高大威武,而且英俊,一身密而长的被毛像绸缎似的披在身上。狭窄、肮脏的空间大大形影了它的形象,但不失一种俊美,大大的双眼,明亮的目光,硕大的头颅……让人喜不自禁。幼崽抬起头,长时间注视着杭盖,虽刚刚经历了毒打,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对杭盖的好感。
杭盖给幼崽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敖劳”。
“敖劳”在蒙古语里是“山岳”的意思。
第一轮,只有三头强壮、机敏的幼崽离开了山洞。
洞口依然为幼崽敞开着,没有食物,只有魔鬼似的毒打。在此之前,幼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了,饥饿和地面上的伙伴吸引着幼崽前仆后继地攀上洞口。从洞底到洞口,对幼崽来说不是难事,但它们是否能离开山洞,就看它们能否禁得住一脚两棒的毒打。尽管这种毒打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可毒打带来的疼痛却是刻骨铭心的。一时间,住地上空回荡着幼崽近乎绝望的嚎叫。嚎叫持续时间之久,嚎叫之惨烈超出了想象。嚎叫声中夹杂着沉闷得如同木棒敲击大鼓的响声。
嚎叫令住地附近的小动物魂飞魄散,清一色停下各种动作,甚至包括追杀与被追杀这种危及生命的行为,纷纷举起头,观望四周,寻找恐怖声音的来源。它们很快弄明白恐怖声音来源的方向,更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甚至想到灾难将要殃及到自身,随后如闪电似的钻进草丛。从草丛里传来惊人的“刷刷刷”的逃遁声。
毒打令来到地面上的三头幼崽极度的恐慌,最初它们还心不在焉地走动着,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跟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很快,不适代替了无所谓。又因为毒打持续时间之长,之残酷,不适被无限地放大,最终被恐慌代替了。三头幼崽低垂着头,弓着身子,凑到一起,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地吟叫,目光不时地瞄向杭盖那里。
说来也怪,幼崽离开山洞,又遭遇如此的惨景,竟然没有离开住地的意思,更没有远遁的想法。
幼崽从小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山洞里,注定它们无比强大的同时,也注定它们无比的孤单。它们本应在认识这个世界时,却被送入黑黢黢的山洞,体验到的是恐惧、黑暗、孤独、饥饿……当它们突然来到这个世界,显得是那么的茫然无知,茫然无从,对魔鬼杭盖产生了深深的依恋,甚至对黑糊糊的山洞也产生了无法说清的好感。当天,离开山洞的幼崽无法找到舒适的过夜之处,又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山洞里。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里,有几头幼崽无法适应皎洁的月光,不敢入睡,再次跑回到山洞里。
一年的山洞生活和一心想着复仇的杭盖破坏掉了这些幼崽身上的很多品质。
又有两头幼崽离开了山洞。
两头幼崽顾不得火烧火燎地疼痛,奔向三头幼崽,长时间嗅闻着,久久不愿散去。这本应该早早享受到的团聚,早早就能表现出来的亲昵动作,整整被往后退迟了一年的时光。即使像嗅闻这种亲昵的动作,幼崽表现得也是那么的笨拙。
每天,住地都上演着毒打与被毒打的一幕。杭盖似乎很乐于这项运动,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不知疲倦地来往于每个洞口之间。看上去,他高大的身材显得过于蠢笨,可事实并非如此,他行动起来,身手灵敏,榆木棒子就像长了眼睛,来去自如,准确无误地落在幼崽身上。
越是出洞晚的幼崽,越是遭到更多更残酷的毒打。杭盖执行起来一点儿不含糊,他要让幼崽明白,你不够强大,就理应遭到毒打;如果你够强大,遭遇毒打的就不是你。
最后一个离开山洞的幼崽来自于八号洞。
八号山洞的幼崽其貌不扬,与其他幼崽相比,身材瘦小,被毛杂乱,目光狡黠。
杭盖给幼崽起了一个灰溜溜的名字——“毛依罕”。
“毛伊罕”在蒙古语里是“丑丫头”的意思。
九头幼崽中,遭受最多毒打的就是幼崽毛伊罕了。同时,它也炼就了丰富的对付杭盖的经验。幼崽毛伊罕一探头,杭盖的大脚就飞了过去。杭盖憨性十足,绝对先是一脚,然后再是两记榆木棒子,程序上丝毫不乱。幼崽毛伊罕心中有数,“倏”,身子退回到山洞里。杭盖踢空了,差点儿折进山洞。幼崽毛伊罕再一纵身,出现在洞口。杭盖挥棒砸下去,动作与之前相比,缺少了流畅,木棒又砸空了。幼崽毛伊罕再次退回到洞里。杭盖“噗哧”一声,笑了。就在这时,幼崽毛伊罕蹿出洞口。
幼崽毛伊罕再一次智取,躲过了对它来说无疑于越不过的鬼门关——榆木棒子。
现在,九头幼崽都离开了山洞,它们没有奔跑,也没有逃离,而是齐刷刷地聚在一起,呆头呆脑地注视着魔鬼杭盖。
不远的逝去
——长篇小说《野狼》创作谈
我时常沉浸在童年的记忆中:村子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潺潺流淌。时而有银白色的小鱼跃出水面,身子与阳光交错瞬间反射出金灿灿的光晕,令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暖色。小河的一面是绿油油的耕地,一面是开阔平坦的草地。草地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土丘。因土丘的出现,一马平川的草地有了线条般的柔美,更因绿色深浅不一的变换,配合阳光的亮与暗,即使单一的碧绿色也变得异常丰富。
站在土丘上,眺望远处,绿色中点缀着明亮的水面——隐藏在牧草中,面积大小不一的水泡。或者说原本一片明亮的水面,因不小心绿色的渐入,打破了整体如一的水面。总之,水泡与草地交相辉映。那上面总有鸟类的翅膀为其添光增彩。而鸟类的天籁之音,配合夏虫的鸣叫,有种空旷、久远之感。水泡与草地相间的尽头仍是土丘。如果有足够的体力和时间,一直走下去,那依然是完美,而又变化多端的翻版吧。
童年中,我出于好奇,曾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寻找它们的尽头,那只不过是让我很失望,但也令我很兴奋的一次寻找。它让我的童年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如果它们有尽头,那也是天与地的交接处。这次寻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我多次去草地深处游历,见证了我童年的那个梦想:她的确没有尽头,永远值得你去寻找。如果你心里还有梦想的话!
后来,随着我的儿童文学创作倾向于动物小说。我认识到,童年我所认识的特殊地形,用一个较为专业的术语形容:湿地。但当地人更喜欢称它为“草甸”。
湿地、森林是地球之肺。
的确,那时生存环境很美,生活很清贫,但幸福指数却是最高的。人们对生活知足,心态平静,对物质没有过高的奢求。尽管很多物质唾手可得,但人的愿望只是用来满足温饱就足够了。孩子们的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与无忧无虑,像接近母体一样接近大自然,熟知大自然,喜欢大自然。童年是最初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恰恰与大自然结合,除了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与印象外,更多的是难以用语言描绘与大自然的亲近感,那是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敬畏。
我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了草地上的小动物,甚至包括草地上的大型动物——狼。我还认识了来自天空的鹞与鹰。天空应该是草地的一部分吧。但很遗憾,我也很诚实的承认,至今对于一些小动物,我无法确切叫出它们的名字,只能依据当时的习惯命名。这种习惯更多的是来自于父辈们对它们的认识与命名,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与传承下去。当然,对于这些至今仍无法叫出确切名字的小动物,并非它们是多么的难得一见,而是很普通。知识上的残缺并不只限于动物,还有包括身边的草类与野花,那是极其普通的。至今在城市里仍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我却无法用准确的名字称呼它们。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我对它们的钟爱。
自然永远是广袤与博大的。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生活日渐改善,而且日渐富裕。这是人所希望的,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我再去小河看看时,随着岁月的流逝,河岸变矮了;河床长高了,最终与耕地融为一体,甚至有的已过早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应归功于风与水的作用吧,水的消失,令风搬来了尘土。一句广告词说的非常好,“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带着某种目标时,人能改变自然。
与小河相继消失的还有草地、水泡、土丘……最终,草甸变成了耕地。当然,随着草甸消失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植被与动物。植被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随着草甸消失,我仍能一如既往地看见它们的身影。动物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但很遗憾,这一庞大家族的种类与数量正日渐萎缩。草甸消失后,我多年去草地深处寻找它们的身影,但令我失望的是,我没有清晰地看到过它们的身影,即使匆匆相随,它们倏的跳出草丛一瞬间,留给我更多的是模糊的身影和惊悚。如果没有童年这段经历,这段经历没有给我留下鲜活的记忆,连我都难以相信,原来草甸有如此丰富的地形与地貌,还有多得数不清的小动物。但这些动物随着草甸彻彻底底的消失了。让我只能在记忆中,一次又一次回忆起它们的容貌。
前年,我去草地游历,无意中又见到了童年记忆中的草甸,但无论它的面积,还是地形,都变得单一而又单调。它坐落在几乎是四周环抱的土丘间。翻过土丘是一望无际的耕地,没有水泡,也没有草地。土丘起伏不定,因干旱少雨,大部分土丘裸露,这与我童年里土丘的容貌大相径庭。不过,那一片偌大的水泡,水泡中茂密的芦苇与蒲草,让童年的记忆变得鲜活,而且充满绿意。从我眼前一掠而过的水鸟,及时添补了记忆的空白。那时,它们常常被我忽略掉,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而我更喜欢飞鸟大家族中高傲的物种——鹰与鹞。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童年里不曾看到一件物品,而且草地上随处可见——围栏。偌大的一片草地,被一个个封闭的围栏围了起来。这象征草地属于某个家庭。有了围栏的保护,牧草长势旺盛。
即使水泡这里,依然有围栏。围栏已深入到水泡中央——那里,也被分割开了。的确,这种承包式的草地,既能够很好的保护草地,又避免了无节制地开发,与己与大自然,都是件好事。
水泡四周散落着一些住户。住户的居住不是象征古老游牧民族的蒙古包,是砖木混合的永久建筑,与小镇上的房屋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好像印证了一个当下的道理:富裕生活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但愿不是这个道理。
以童心守望草原
——许廷旺和他的“动物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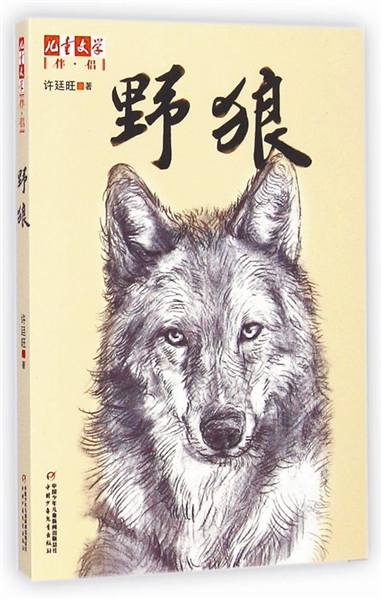
文/陆文学
许廷旺作为内蒙古少有的70后草原作家,近年出版的数十部儿童文学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写动物,写草原,其实是在抒发作者的故乡情怀,作品全景式呈现一部部挑战命运的生灵史,一曲曲永不言败的生活长歌。翻开它,你将看到不一样的草原,不一样的动物世界。近日,作者的新作《野狼》荣获通辽市首届“科尔沁文化政府奖”,可谓实至名归。
创新之路:对儿童心灵版图的新拓展
作品《野狼》,写一个颠沛流离的马匪,为复仇驯化狼犬,在一个个寒冷而危险的冬天过后,走出草原,演绎出情节跌宕的故事。这不仅是草原上人和动物、人和人的故事,而是自然界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作品以爱恨交织的人性开篇,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人与动物的距离,更展示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也好,马也好,狼犬也好,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在生态的链条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许廷旺的动物小说忠于现实,作者记述草原牧民的爱恨情仇的同时,也对社会上的某些不良风气,如见利忘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进行了批判。成功实现以单纯文体处理厚重题材的新尝试。
作品真实地展现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片草原,有这样一群动物,它们和一群充满了灵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故事吸引我们的,不仅是那些多彩的生活,而事实上,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动物与人同样被流淌在血液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荒凉的大草原里,忍受着极端的天气,挑战人类生存的极限,是一群真正与大自然对话的人。”
许廷旺的创作探索一直行进在瞩望高峰、不断成长的路上。丰盈的创作成果离不开创新的实践与努力。当人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诠释世界的内涵而努力。这篇动物小说集智性与知性于一体,把动物小说创作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并以此唤起儿童读者的审美惊奇,在吸纳众多观念的基础上对儿童文学精神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因而也就推动儿童文学创作在更多维度上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
人文之笔:对动物题材的新尝试
许廷旺的小说以叙事性见长,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聚焦于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的关于生与死、爱与恨的生命纠缠,跳出一般人类故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情节模式,在精心铺垫的场面与环境中展现力与力的正面对决,使许廷旺擅长的悬念营造手法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接踵而至的惊险场景衔接而成的小说,屡屡让人目不暇接,手不释卷。
在这些展示牧区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把目光聚焦到草原,把广袤草原的深邃魅力展现给读者,与一般的动物小说的主要区别是,作者在用拟人手法虚构一些动物故事时,让人走进动物世界,在表现动物的智慧和感情中,融入作者的生活理念,使得人与动物的沟通更富有生活内涵。
许廷旺的动物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将动物当动物写,又努力通过动物、动物与动物间、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写人、写人际关系,他着重表现的是动物和我们生活中某些人、某些人际关系相重叠的部分。他写与人最为接近但又充满野性的动物,通过它们的行为反映动物与人、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和动物的故事既是自然界的故事、人性的故事。从而反映出大自然的组成在生态的链条上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些忠于现实,展示自然的生态文学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作者的动物小说的叙述方式。
自然之恋:对生态环境的再思考
作品《野狼》通过动物小说形式,记述了草原游牧文明的鲜活动态、生命永恒、及内蕴的张力。这是对已忘记初衷的人类一个提醒:敬重我们的母体大自然。作者以其对草原动物的生动再现和草原人文的美好升华,激活了常年生活在钢筋水泥大城市中的大众对于异域空间的神奇体验,而充沛的叙事情怀和深入的生态思索又使得读者对于作者精神世界的游历充满了兴趣和乐趣。在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世界,这样的动物故事的出现恰得其时,为时代奉上了有益的文学濡养。
许廷旺的作品语言朴实生动,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作品塑造出一批有责任心、有爱、有智慧的草原社会现象,给读者打下深刻的烙印。他的作品里,蕴含着草原文化的深邃神秘,字里行间中,充满草原人的热情豪放。一部部栩栩如生的文字深刻地反映出作者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告诉我们除了人类外,地球上还有许多生命是有感情有灵性的,它们有爱的天性,会喜怒哀乐,甚至有分辩善恶是非的能力。我们应当学会尊重动物,尊重另一类生命形式。这一理念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显得更有艺术价值和思想高度。以童心守望草原。许廷旺的作品充分彰显出作者的强烈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作者系通辽市政协文史专员,首届“科尔沁文化政府奖”评委)
责任编辑:苏伦高娃
Copyright © 2015 · All Rights Reserved · tongliaowang.com